- 科技報導
- 精選好讀
文章專區
2025-07-15新階級社會《創新之後:當水電技師、護理師與維修工程師成了稀有人才》
523 期
Author 作者
李.文塞爾(Lee Vinsel)、安德魯.羅素(Andrew L. Russell)
拉爾夫在美國中西部一所大學的IT部門上班。身材魁梧、頭髮灰白、蓄著一口落腮鬍的他,從不在意外型與打扮,總是穿著一條牛仔褲配一件T恤。拉爾夫在鐵鏽地帶鄰近芝加哥的一處貧窮小鎮長大,在他童年的記憶裡,鋼鐵廠早已倒閉多時。他大學讀的是物理,畢業後換過很多份工作,最後在IT產業待了下來。拉爾夫所有的電腦技能都是自學來的,他從新人時期每小時十二美金的最低工資一路往上爬,現在是年薪超過六萬美元的受薪階級。
拉爾夫喜歡這份工作,有部分是因為他的同事,他們都樂於助人,也都不是愛出風頭或好求表現。IT從業人員的挫折感很大。「這一行的人總是說,爛軟體怎麼修也還是爛。」拉爾夫說。反而是同事之間的情誼,讓這份工作值得繼續做下去。
IT團隊謙恭有禮、寬大為懷的精神在他們服務的對象身上並不常見,有些客戶會要求問題立刻解決,還會把錯怪到IT人員的頭上。拉爾夫說,有些使用者只要一看到錯誤碼,就會打電話到他的辦公室,說不曉得發生了什麼事,一定是IT部門出錯。即使錯誤碼已經清楚註明是使用者的操作問題,例如不小心修改到電腦的核心檔案,但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的責怪還是會照常發生。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一些最傷腦筋的要求還是來自資訊科學系。那些教授視追求創新為己任,經常要求IT部門做一些辦不到的事,例如無止盡地加快網路速度,而且都以高人一等的語氣來下達指令。
有位教授抱怨他的系統運作速度太慢。IT團隊卻發現,他操作的網路程式同時連接了多部電腦,資訊從A點傳送到B點需要時間和運算,畢竟硬體系統是遵守物理定律的。據拉爾夫說:「絕不可能比用單機操作還快。」但是教授好像不明白這一點。
問題在於,實際在多台電腦上操作時,學術理論的預測不一定管用。拉爾夫直言不諱地表示:「資訊科學算不上是科學,很多教授壓根就不曉得電腦是怎麼運作的。」當IT部門收到無理的要求時,拉爾夫說:「你必須以最有禮貌的方式讓對方知道,你真是他媽的蠢到家了。」教授們的想法乃源自於美好的理論世界,可是他們卻不願意動腦筋想想,要怎麼做才能在現實世界中實現。
拉爾夫是那所大學的重要人物。他要負責維持四百五十部Linux機台的運作,其使用者主要是粗手粗腳的大學生,還要負責維護多台虛擬電腦。話雖如此,在校園裡走路有風的卻是那些尊貴的教授。學校官網貼滿了與創新論有關的文章,包括某位教授的研究成果,以及校方為學生舉辦黑客馬拉松、程式設計營的活動公告。不用說也知道,那些確保校內電腦運作無礙的人,並沒有出現在網頁上。儘管IT人員的勞力付出至關重要,卻總是被漠視、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工作。
拉爾夫的體驗也是許多人的親身經歷。在社會與組織的內部,維護工作經常是落在最底層工作人員。維護人員都曾被忽視、使喚、佔便宜並忍受對方的高傲態度。有很多機構會規定工友及維修工人必須穿連身工作服,以顯示他們的身分是維護人員。這種傳統的做法與心態是怎麼來的?
萬般皆下品
早在人類文明出現以前,地球上便已經存在分工的現象。舉例來說,螞蟻有工蟻、雄蟻、蟻后,蜜蜂有工蜂、雄蜂和蜂后,其職責皆不同。專家在研究收穫蟻(harvester ant)後發現,牠們當中會有不同的群體來負責執行覓食、巡邏、修復蟻巢、及維護蟻群垃圾堆(refusepile)。請注意,在這四種工作中,有兩種很明顯是屬於維護工事。
人類也是從很早以前就有分工的現象。狩獵採集社會從古至今都是以性別來做為分工的基準。但是,隨著社會愈趨複雜、出現階級之分,維護與清潔工作的分配也變得愈來愈不平等。舉例來說,在古希臘時代,柏拉圖主張,哲學家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有閒暇時間(skhole)去尋求知識,這個字流傳至今,便成了學校(school)一詞。這些哲學家能自由地沉浸在自我與知性的世界中,全是因為有奴隸和僕人代勞做家事。隨著時間過去,西方世界便區分出「腦力活」與「體力活」:前者是上流階級的職業,後者是卑賤的體力勞動、粗活,是下等人的工作。
包含維護及維修工作在內,職業的位階在封建社會最明顯。從印度的種姓制度來看,達利特(Dalit)是「穢不可觸」(untouchable)的賤民,必須徒手清理衛生設施,包括戶外廁所及排水溝。而這種不乾淨又危險的工作有百分之九十是由女性完成。這些拾糞者(manual scavenging)常會因為吸入有毒氣體引發窒息而死。
然而,印度社會絕非世上唯一有種姓制度的社會。在葉門,阿哈丹(al-Akhdam,字義為「僕人」)是被排擠的弱勢族群,只能夠從事清掃街道和洗廁所等骯髒下賤的工作。有一句葉門諺語顯露出他們的社會地位:「盤子要是被狗碰到就拿去洗,要是被阿哈丹碰到,那不如把它砸了。」如今在世界各地,還是有很多國家持續實施類似的種姓和階級制度。
我們不應該自欺欺人地說,美國及其他西方社會就沒有階級制度。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美國以前是奴隸社會,那時是由黑奴來負責各式各樣的維護工作,包括做家事。但是,奴隸制度的終結並未連帶地廢除社會階級,而職業也依然有高低貴賤之分。舉例來說,在維吉尼亞和偏南方的幾個州,有些工作現在依然不適用於該州的最低薪資規定,包括飯店門房及保姆幫傭—也就是在傳統上是由非裔美國人擔任的工作。
社會學家自一九二○年代,開始研究各種職業聲望(occupational prestige),以調查各種工作在美國人心中的社會地位。在一項歷時多年的研究中,研究人員請諸多受試者按照自己的既定觀念為二十五種職業排序。結果發現,即使研究已執行了數十年、取樣範圍涵蓋全美各地,眾人心中的排行次序還是十分相似,幾乎沒有什麼變動。銀行家、醫生和律師等腦力工作者總是名列前茅,工友、泥水匠及挖水溝的工人總是吊車尾。維護性職業,例如水電工及理髮師,則是一律屬於後段班。雖然這類工作對社會運作十分重要,但人們卻寧可眼不見為淨。正如某位社會學家所說:
「這些會弄髒手的工作是社會的基礎,但卻沒有機會進入溫文爾雅的公眾對話空間。人們心照不宣地將這些苦差事放在社會的角落,並汙名化相關的從業人員。」
不過,有些工作的名聲,尤其是與科技有關的,確實隨著時間過去而有了改變。舉例來說,在早期的美國歷史中,技工與電匠的地位頗為崇高,也是能出人頭地的工作。但正如歷史學家凱文.博格(Kevin Borg)觀察到,到了今天,大家會叫成績不好、找不到出路的學生去當汽車維修技師。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這把貶低技術工作的火不斷燒下去,有天也會燒到今日世人眼中的熱門工作。記者克萊夫.湯普森(Clive Thompson)的文章〈寫程式會成為下一個藍領階級的主流工作〉(The Next Big Blue-Collar Job Is Coding)在網路上引起熱烈討論。湯普森在該文中指出,很多IT工作的性質跟藍領工作很相似,而相關的訓練可能會變得更側重實務。即使是在今天,大部分的IT工作也都還以維護為主。而湯普森強調,愈來愈多人擠進IT產業,必將導致從業者的薪資及報酬降低。
有些職業雖然現在看似穩定,但隨著時間過去,還是有可能出現變化。既然人們對於職業排行與位階的看法一致,那這樣的直覺究竟是從何而來?原因有很多,但關鍵在於,工作的階級觀念是經由學習而來的。
受到理察.斯凱瑞(Richard Scarry)創作的童書《好忙好忙的小鎮》(What Do People Do All Day)所啟發,社會學家約翰.萊維.馬丁(John Levi Martin)在著名論文〈好忙好忙的動物〉(What Do Animals Do All Day)中建立了一組資料庫。在斯凱瑞的忙碌鎮(Busytown)中,每個動物各司其職,馬丁分析了牠們的配對模式,並發現當中的關聯性。假如你是鎮民,肯定會想要成為獵食者,因為鎮長和機長都是狐狸;醫生是獅子,開的是荒原路華高檔車。那麼,最需要體力的藍領工作是由哪種動物負責的呢?答案是身分卑微的豬,而馬丁認為牠代表了「美國的工人階層」。在故事中,豬必須做別人瞧不起的勞力活,包括清掃下水道,還時常惹出麻煩,引發不幸事故。斯凱瑞筆下的人物貝先生(Mr. Frumble)老是笨手笨腳、把場面搞得雞飛狗跳,而牠正是一隻豬。
馬丁的文章很有趣,有些段落讀來令人莞爾一笑,但內容要表達的事情很嚴肅。他在文章中提到:「在閱讀忙碌鎮的故事時,孩子們學到大人們每天做的事,也學到哪一類人會做哪一種事。」換句話說,大人騰出時間來為孩子朗讀這本童書時,也正在向孩子灌輸職業階層(occupational stratification)的觀念。我們無從得知斯凱瑞的配對方式是有否任何用意,但他也許只是在無意間把小時候被灌輸的職業階級觀念寫進了書裡。
除此之外,我們也會從其他地方認知到哪類人該從事哪種工作。我們有個朋友住在曼哈頓的摩天大樓,她不時得向小女兒解釋美國的種族情況,因為大廈門房和打掃阿姨老是由非裔美籍人士擔任。這些日常經驗不斷累積下,這個孩子會以為非裔美國人只能做這些工作。
當然,同樣的工作在其他地區會由不同族群負責,在美國境內也是。我們兩人都經歷過漂泊不定的學術生活,從青少年到四十歲搬家過很多次。在伊利諾伊、紐約和維吉尼亞州的鄉下地區,我們注意到,像工友和速食店店員這樣低技術性的工作,主要是由中下階層的白人來做,青少年也不少。在芝加哥和紐約市區,這類工作通常是少數民族或移民在擔任。但不管在哪個地區,唯一不變的就是這些職業的相對地位。所以你不會看到中西部的農場工友開鍍金的豪華名車,而醫生開著快要解體的破車在閒晃。
就業市場確實有社會階層的區分,我們在青春期時,肯定已經清楚了解,哪些職業是落在社會的哪個位階。這是長大成人的必經之路,也是在社會生存的基本認知。而這類知識大多是從家人以及社交生活中學來的。不過,這一切都要等到我們進入學校、尤其是上大學以後,才會有實際的體悟。
偏離現實的大學教育
創新論的意識形態滲透到美國文化的各個層面,它對教育制度的衝擊特別強烈,從學齡前教育到博士學程,並強化了創新者與維護者的地位差異。在美國,創新論會與STEM掛勾,也就是科學(science)、技術(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及數學(mathematics)方面的教育。一般認為,教育單位強化STEM領域,就能維持與增進國家的創新力,孩子長大後也更容易找到好工作。學生們被鼓勵去參加黑客馬拉松、程式設計營、機器人社團等有助於培養創新潛能的課外活動。許多流行一時的教學熱潮,譬如K–12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 K-12),以及大學院校新成立的單位,例如詹姆斯.麥迪遜大學的X實驗室(James Madison University’s X-Labs),都號稱能開發學生的「創新能力」。
在第二章裡,我們特別強調,創新成果不能只歸功於少數天賦異稟的創新者,而且那樣的能力也無法傳授。愛迪生、尼龍發明者卡羅瑟斯(Wallace Carothers )、名主持人歐普拉與媒體人赫芬頓(Arianna Huffington)並沒有共通的能力或技能。不管是善於交際、容易找到成功機會的外向人士,還是寧可在家自虐也不想去參加派對的內向者,都能發明新玩意兒。
詹姆斯.麥迪遜大學的X實驗室宣稱,他們能傳授通用的「批判性思考法」,但其成效也一一被其他專家打臉。7絕大多數的創新都由有經驗、有改革決心的專家一點一滴累積出來的,沒有什麼捷徑能省略幾十年的訓練和努力。
不過,比起推廣站不住腳的教育方法,大專院校一味地推崇創新概念,才是問題的根源。大部分的學生在畢業後的工作都與創新無關,但都對社會很重要。過去幾年,我們在大專院校舉辦過多次講座來介紹維護者這個組織。每當我們問到,有多少人畢業以後想要成為技工、電匠、IT支援人員等維護工作者時,總是沒有人舉手。這些當然是玩笑話,畢竟同學可不是為了糊口飯吃才來念大學的,但我們想讓他們用更開闊的角度去思考未來的志向。而許多學生以為自己將來會成為創新者,只是因為有人不斷在灌輸那樣的觀念而已。
我們兩個人在二○一二年到一六年任職於史蒂文斯理工學院,尷尬的是,校方還自封為「創新大學」。該校工程學系的大四生在發表畢業專題報告時,還必須說明自己的作品具備哪些創新精神。但不用說,絕大多數的專題內容根本談不上創新,學生們只有學到如何在胡扯與吹牛中自我推銷。事實上,創新者最重要的技能,就是表演和吸引他人目光,讓自己的作品看來很神奇;這一點稍後會再討論。
不過,更深層的問題是,史蒂文斯的創新評分嚴重扭曲了工程領域的本質。鐵一般的現實是,百分之七十的工程師都是負責維護及監管系統運作,只有少部分工程師在從事創新和研發,特別是「研究」那個部分。因此一般來說,工程師是維護者與操作者,而非創新者。
這種情況也出現在最熱門的資訊工程領域。根據資料顯示,各大機構的軟體預算有百分之六十到八十是花在維修項目上頭。許多資訊科系的畢業生都是進入非軟體領域,例如IT基礎建設、使用者服務以及網路工程。換句話說,他們最後從事的是維護工作。既然大學設立是為了追尋真理,那麼老師們就應該以務實的角度帶領學生了解真實世界的樣貌,以及校友的就業情況。校方或許可以設法加強學生的維護觀念,並突顯營運工作的價值,畢竟大部分學生都會投身這些領域。
另一個迷思影響更深遠,在許多層面上也與創新論有所關聯,即不上大學就會擠不進中產階級。雖然大學畢業生通常賺得比從事技職工作的人來得多,但考慮到其他因素的話,就沒這麼絕對了。舉例來說,就讀職業學校的平均花費是三萬三千美元,若要取得學士學位,則須花費大約十二萬七千美元,也就是包含學費、生活費和學貸利息。此外,有百分之七十的學生背負學貸,其中有百分之二十的金額超過五萬美金。這些貸款和利息往往需要花幾十年才能還清。再說,美國技職學校一般只要讀兩年就能畢業,比起讀四年制的大學,前者至少可以提早兩年出社會賺錢。更別說不少大學生得花五年以上才能拿到學位,還有更多人讀到一半就被退學。
讀大學是享有體面人生的唯一途徑,這樣的迷思並非為美國人獨有。西澳大學工程系教授梅琳達.霍德凱維奇(Melinda Hodkiewicz)憑藉執業工程師與學術研究者的雙重身分,鑽研維護這個主題長達數十年之久。她向我們提到,澳洲的高教政策在二○一○年代大轉彎後,可以上大學念工科的人就變多了,去接受職業訓練的人自然就變少。這引發了幾種意想不到的不良結果。一方面,數理能力低落的新生經常無法應付紮實的數學與科學課程,另一方面,社會上也迫切需要各行各業的人才。霍德凱維奇感嘆道:「這麼說有點殘酷,如今我們養出了一批找不到工作、也不會有人想要的大學工科畢業生。但他們也從來沒想過要去當稱職的技術人員。」
人們有時會一頭熱地主張,社會需要培養更多技術人員。過去十年,技術斷層(skills gap)的討論就從沒斷過,也就是說,例如焊接工及電匠這樣的技術人員,數量一直趕不上整個產業的需求。近期也有研究指出,技術斷層實際上並不存在。總之,專家們還是會繼續爭論這個話題一段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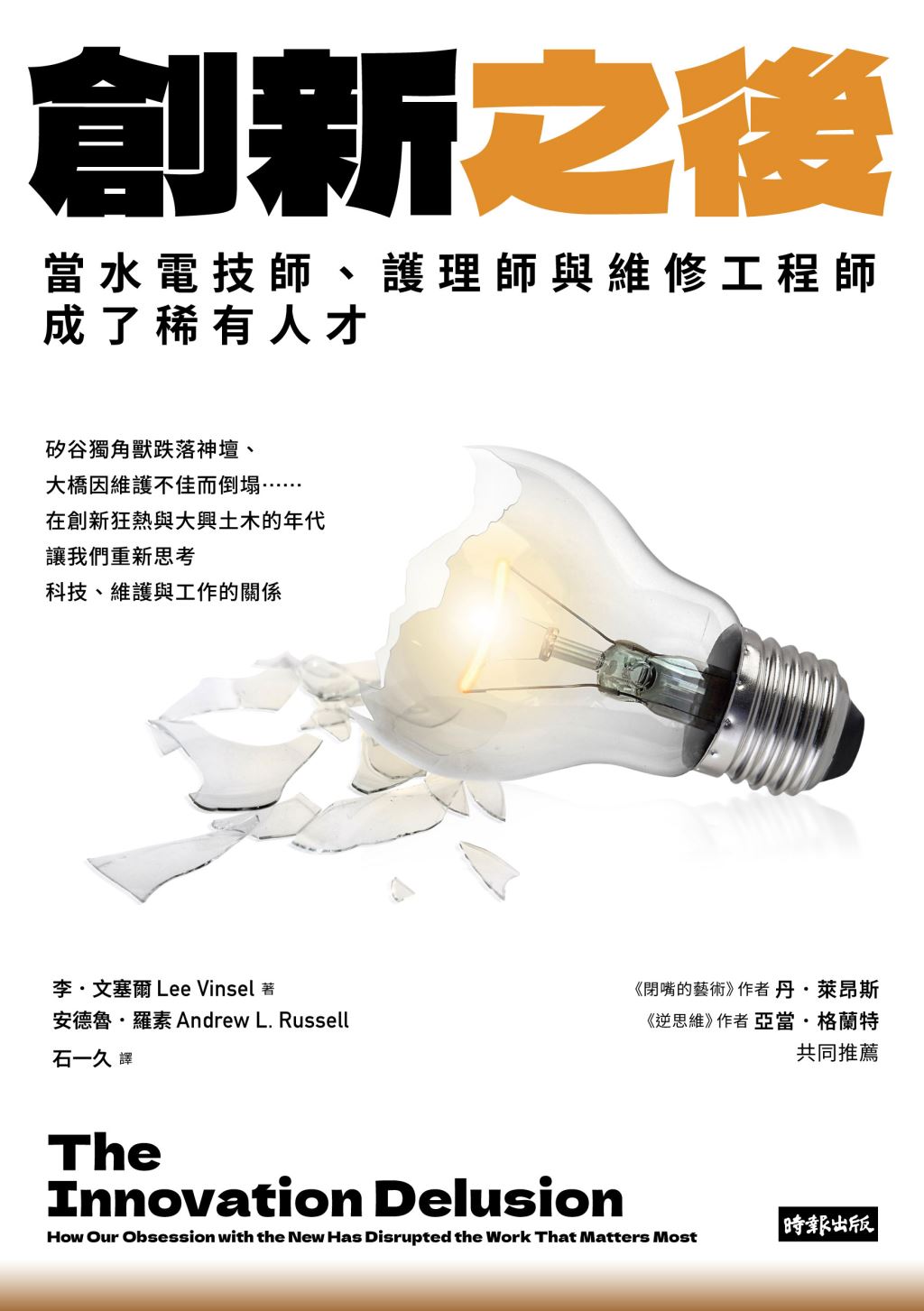
書 名|《創新之後:當水電技師、護理師與維修工程師成了稀有人才》
作 者|李.文塞爾(Lee Vinsel)、安德魯.羅素(Andrew L. Russell)
譯 者|石一久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5 年 6 月
創新和發明是人類文明的推力,但從網路與科技業成為顯學後,諸如 「破壞性創新」、「快速失敗」成為各大公司的信條,而維護工作反 倒被忽略,正如《庶務二課》和《IT狂人》中被打到冷宮的工作人員。 科技史學家文塞爾和羅素觀察到,現代人對創新的執著,不但令生活 更空洞、而且更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