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報導
文章專區
2020-04-10一個春季學校與一場研討會的背後-顧正崙、呂理帆、楊皇煜專訪節錄
460 期
Author 作者
蔡孟利/科學月刊編輯委員。
長庚紀念醫院林口院區、長庚大學、中華民國免疫學會以及中華民國癌症醫學會於去(2019)年4月9~11日在臺北圓山飯店舉辦福爾摩沙免疫春季學校,並於4月12~13日在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舉辦福爾摩沙免疫春季會議,這兩個活動簡寫均為FISS(Formosa Immunology Spring School & Symposium,http://fiss.mystrikingly. com/)。此類學術活動在臺灣很常見,但FISS所邀請的國外講者陣容龐大,兩個活動也接續舉行,整個FISS期間長達五天,這在臺灣學術圈活動來說,倒是有些稀奇。
看到這樣的盛會在臺灣舉辦,一開始只是跟想幾位主要籌辦人顧正崙博士、呂理帆博士、楊皇煜醫師聊聊籌辦動機,然後寫篇例行的報導告訴大家有這件事而已。沒想到透過登門拜訪與越洋視訊,總共四個多小時的訪談中,居然談出超過 65000 字的話。
筆者算修稿很快的人,但這次整理逐字稿卻出奇的慢。因為看著那些談話的文字,腦子就不斷地回味在訪問的時候,感受到籌辦人員們那些會賺人熱淚的壯志,以及為臺灣細膩付出的豪情。整個FISS所完成的不可能的任務(mission impossible),是筆者這兩年在臺灣學術圈內所看到最感人、最熱血的事情。
完整訪談版本詳見:
1.〈一個春季學校與一場研討會的背後(上)- 顧正崙、楊皇煜專訪〉,《科技報導》,https://scimonth.pse.is/R5NEN。
2.〈一個春季學校與一場研討會的背後(下)-呂理帆專訪 〉,《 科技報導 》,https:// scimonth.pse.is/NPCLJ。
顧正崙博士(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副教授)、楊皇煜博士(長庚醫院副教授兼醫學研究部副主任)訪談節錄:
話題一:談「春季學校」的輪廓
春季學校基本上像是菁英教育的概念,首先我們先選一些比較優秀的學生,讓他們接受大師的一對一指導。這些大師的東西,你聽他講還好,因為他們都寫過很多論文(paper)跟文獻回顧(review),跟他在台上講的內容差別不大。但春季學校的概念是可以跟這些大師很近距離的、一對一的接觸,所以我們在挑選學生的時候非常的認真。邀請這些大師非常困難,因為他們不缺人邀請,平時也很累、很忙,即便答應要來,基本上能給個兩三天就很不錯了,但這次這些大師們都從頭待到尾。我們國內找的是中研院謝世良老師;國外十個講者,有四個是美國國家科學院(NAS)院士,其實NAS院士在免疫學領域也沒有多少人,我們一口氣找了四個,而且FISS剛結束,其中一位講者寇隆納(Marco Colonna)也成了NAS院士。可以托大的講,最近在亞洲至少我知道的就有兩、三個免疫學校,我們絕對不是花錢最多的,但講者陣容絕對是最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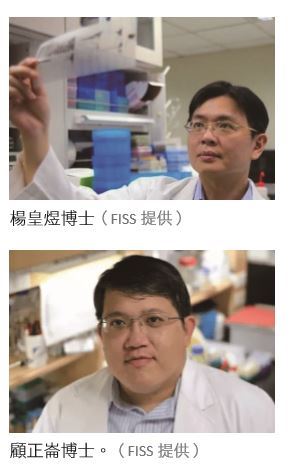
話題二:值得與大家分享的活動細節
春季學校有三件比較特別的事。
第一件是壁報論文展示(poster session),讓這些大師親自來看學生的壁報。原本表定一個半小時,結果十位大師都親自下來看,而且欲罷不能。基本上每個人都把每一張壁報看完,所以每一個學生要講幾次呢?要講十次。這還不夠,我們五位旅外的臺灣學者呂理帆、何秉智與路景蘭等人也是一張張地看,所以每一個學生要以全英文報15次。以這些大師來說,是不太可能在會議中出席壁報論文展示的,相當罕見。
所以學生們非常的興奮。要知道,今天你做調節T細胞(regulatory T cells),評你壁報的是可能會得諾貝爾獎、研究調節T細胞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盧登斯基(Alexander Rudensky)博士,能讓他跟你討論,真的太難得了。而且我們並不是只找十個有名的人來而已,也盡量涵蓋所有免疫學的領域,基本上我們有T細胞(T cells)、B細胞(B cells),有自體免疫(autoimmune)、先天免疫(innate immunity)、巨噬細胞(macrophage)、神經退化(neurodegeneration)等,同樣的課題被從15個角度討論研究,這是第一個很棒的地方。不只是學生,這些大師們有多滿意呢?滿意到時間結束後去吃飯,他們都不肯離開,原定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延長到幾乎四小時,其中一位大師舍滬特赫(Hilde Cheroutre)跟我講:「我沒看完你不准給我關燈」,而圓山超時要加的錢可是要四、五萬塊喔。
第二件是,我們隔天安排一個口頭報告,也是選了5位學生上去, 報告中的攻防過程非常精采。雖然學生因為沒有經驗所以比較像是被屠殺,但是學生還是從那邊學到很多,被神人屠殺也很爽!
第三件事就是提升互動。用餐時我們做了一個非常棒的事情:抽籤入座,包含那些大師。每一餐大家都打散,學生們互相不認識,大師們跟學生也可能是第一次見面。三天晚餐都是以這樣的方式進行,所以學生跟每個大師都有機會見面,這才是真的交流。很多人從第一天就講,以前都覺得這些人高不可攀,結果沒有想到,從第一天開始就覺得他們也是可以一起喝喝雞尾酒聊天的朋友,我覺得這三個活動才是春季學校真正的精華,至於上課的內容,回家看看他們發表過的論文就可以了。
話題三: 別於傳統演講的安排
有個一般人可能不會觀察到的現象。整個活動中,演講者們都表現得比我們預期還積極,舉例來講,壁報論文展示的四個小時中,通常大咖只會在自己的時間直接出現,其它時間都躲起來。但這次,在上課的時候他們會出現,吃飯的時候也是全程跟學生吃飯。
給演講的時候更是如此。在研討會中,你什麼時候看過主議題講者(keynote speaker)給完演講後還在底下坐一整天?這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這些演講者每一個人都超時。這些人給演講都給成精了,每一個人都身經百戰,為什麼會超時?因為他們在拚場,互相不肯認輸,希望能吸引到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學生的注意力、也想吸引到所有與會者的注意力,所以他們基本上是盡全力的。我為什麼會知道?因為我們是這些人的學生,從來沒有看他們這麼努力過。
話題四: 作個細水長流的學術活動
臺灣學術圈有個很大的問題是,我們的制度跟訓練比較扭曲,只聚焦在幾個關鍵績效指標(KPI)。但是學術精神最重要是什麼?在於積極、在於討論、在於天馬行空的想法,我覺得國內非常少做這件事情,所以我跟學生講,這才是你在這個春季學校、在這個會議中學到的,你應該帶回去散給朋友們這才有用,不然這會議結束就結束了、就變成煙火了。國內沒有辦過很好的會議嗎?有啊,很多會議結束就結束啦,那給你帶了什麼衝擊?可能對你自己有啟發,不過對社群沒有啟發。我們要的應該是對科學社群的啟發,不然講句實話,那只是我們花了大錢當冤大頭,請了天兵天將來這邊耀武揚威一番就回去了。
我們這次邀請回來的五位臺灣旅外學者呂理帆、何秉智、黃景政、路景蘭以及駱宛琳,都是極端優秀的學者或是未來之星,可是這些人過去跟臺灣學界的關係沒有這麼密切。以前都是靠個人關係,但這次是有系統地建成一個很強烈的網路,而這件事情能夠辦得起來,主要還是這些旅外學者對臺灣回饋的心。他們在國外累積大量的人脈,大量的資源無處可去,這是給他們一個出口,是給他們回饋臺灣的機會。畢竟,外國人不可能多愛臺灣,但我們這些旅外的臺灣學者怎麼可能不愛臺灣?
話題五: 學生的反饋
會議辦完後,我學生跟我說:「老師我要留下來唸博士班」。我說:「你這麼優秀我們這種小實驗室養不起,你要不要再考慮一下?」他說:「我就是決定要留下來」。
這位學生都得到最佳壁報獎,也就是說這些大師們都很喜歡他,所以他要申請國外的博士班都不是問題,那為何他選擇留下來?因為他們發現有人照顧他們,既然老師在意他們的生涯、關心他們的發展,他們有什麼不留在這塊土地上打拼的理由呢?如果我們支持他們在這塊土地上長大,為什麼還要離家背井?這就是我們辦這個活動為什麼這麼用心,為何花這麼多錢辦到這樣的規模。我們要讓學生感受到「我們在意你」,我對那些天兵天將沒有太大興趣,他們喜不喜歡臺灣其實不關我的事情,但我希望他們喜歡我們的學生,希望學生可以感受到我們真心想幫助他們成功。
自己知道在臺灣當老師不可能得諾貝爾獎,畢竟臺灣的學術環境還有很大進步空間,但也不想當二流的老師啊!我的意思是,幾位旅外同學在國外發展的很好,我為什麼就是要被人家覺得「在臺灣就是比較二流的」?在臺灣當老師有一個很重要的責任,就是照顧臺灣下一代的科學家,這讓我覺得我的工作有意義。
呂理帆博士(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分子生物學系副教授)訪談節錄:
在開始這段之前,容筆者先引用訪談中呂博士的這段話:「正崙在臺灣,他有很多問題要去面對,我們幫不上忙,很多子彈他幫我們擋,我們真的做不了;他說你們在國外講得很容易,最後出了問題,你們拍拍屁股就能閃人根本不會被影響到,但他在臺灣,他會受到影響。我說,我們很抱歉,沒辦法,可是一樣在國外呢,我們要面對這些免疫界的大頭們,和這些人關係的建立都是多年累積下來的,如果跟我們翻臉了,那我們也同樣什麼都沒了。」
如果筆者說,這些臺灣年輕學者賭上學術生涯在為臺灣付出,並不為過。

呂理帆博士。(FISS 提供)
話題六: FISS邀請名單,如何決定?
在說明我們如何選擇邀請外賓前,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我們心中想要的FISS形式。除了要辦個研討會,我們真的想做的事情是籌辦春季學校。其實這並不是全世界第一次有的形式,先不論其它生物學領域,光是免疫學這個領域,在日本理化學研究所(RIKEN)、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Star)跟歐洲都有類似的活動,像RIKEN就是夏季學校、A-Star是冬季學校。之前我有學生跟博士後參加過這樣的夏季或冬季學校,他們的感覺都非常好:那是一個小群體,讓那些在專業上具領導地位的專家跟這些被篩選出來的學員在同一個地方,一個有點與外界隔絕的場所,幾天之中進行很密切的互動。整個過程中,他們可以跟這些所謂高高在上的學界大頭們自由討論,因此他們覺得學習到很多。
這個想法出現後,接下來就要選擇適合的講者。對我來說,不管請來的演講者是不是院士,都必須要有一個能夠橋接他們的人,把他們與學生的距離拉近,因為如果不這樣做,到時演講者們自己聚集在一起講話,學生不敢跟演講者搭話,學生們還是自己跟自己一群,那就算把大家關在同一個房間裡,還是不會有良好的互動。
對這些外國學者來講,臺灣畢竟是一個陌生的環境,要他們突然對臺灣的學生變得很親切這是不可能的。所以那時候的前提是,邀請的學者在科學上要有一定的成就,而且跟我或我們其它在國外臺灣的科學家有私人交情,可以是他們之前的博士後或學生來扮演這樣橋接的角色,再把可以找的人名單列出來。再來,因為畢竟是免疫學的學校,我們不希望人選太偏頗於某個侷限的領域,所以盡可能涵蓋免疫學的每個層面,看看裡面有誰是可能邀請的,再從免疫學的各分項中選擇演講者。
話題七: 談學員數限制的設計
春季學校中就30個學員,然後大家一起相處幾天。但是這些大師既然來了,能不能有其他的輔助方法讓更多人受惠?這點其實是當初我跟正崙在籌備委員會中有很多爭執的地方,正崙一直跟我說可不可以變80個?50個也行。如果是錢的問題,他說我們不一定要花那麼多錢在圓山嘛,為什麼不能在長庚找個演講廳,然後大家住宿舍?我說,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除了要讓演講者覺得今天來臺灣是一個很讚的感覺外,我覺得也要讓學員覺得今天能被選上FISS學員是一種榮耀,而不是一個他們隨時想參加就可以參加的會議。
說到這裡先講一個小故事。今天為什麼會想辦FISS呢?其中有個原因就是當初正崙邀請他的老闆──卡沙諾瓦(Jean- Laurent Casanova),也是我們這次的主議題講者──到長庚給演講,他那時候只照了張照片給我們幾個在國外的朋友(也就是後來的國際籌備委員)看,整個會議室聽他演講的只有20幾個人,其中有一半還是正崙自己實驗室的。以卡沙諾瓦這種程度的演講,如果是在美國,可以想見演講廳是擠不進去的。臺灣能請到這麼好的演講者,為什麼人那麼少?正崙就說:「你們在國外住太久了,完全不瞭解臺灣的現況,你知道嗎,臺灣的演講要千拜託萬拜託學生去參加。」
所以正崙一開始也說,舉辦FISS的想法是很好,但到時候可能沒人想報名,還得求學生、實驗室的人去報名。其實當初想找臺灣的老師幫忙籌備FISS的時候,很多老師雖然不太好意思講什麼,可都或多或少暗示我們到時候可能會失望。所以我那時候一直想的是,要怎麼讓臺灣的學生主動想要參加這個活動。我覺得必須要讓這個活動建立起一種價值感,也就是說讓他們覺得今天被選上是一件很榮譽的事情,所以人不能多。可能人性就這樣,當一件事情太容易了,即使我們的出發點是好的,想讓更多臺灣學生受惠而增加人數,但結果可能就是不會有人在乎與珍惜;但若是這件事情是稀有的,大家就會想要去爭取。

課堂外的餐敘,大師與學員抽籤隨機入席,增進彼此交流互動,是活動裡相當特別的一個設計。(FISS提供)
至於第二個,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希望被選上的學生能有最好的收穫;今天如果80個學生都要能受到照顧,與大師互動的時間就會被稀釋掉,品質就會變差。 我跟正崙說,為什麼是30個人?這不是隨便取數,我的想法是,今天一桌吃飯十個人,六個學生加兩個大師與兩個籌備委員共一桌,這樣五桌的學生總數就是30個人。
我們也考慮到吃飯的座位如果沒有強制,那一定是學生跟學生吃一桌、演講者跟演講者自己吃一桌,這樣一點意義都沒有。所以我們決定:吃飯抽籤,讓每一個學生、演講者與臺灣的籌備委員都抽籤,每一餐會跟誰坐都是隨機的。在這種情況下,每一桌就是十個人(六個學生、兩位大師以及兩位臺灣老師)來達到最好的互動。當然很多人可能會覺得我們好大喜功,要找圓山、要限30個人,覺得純粹我們浮誇,但我們不希望因為妥協導致大家不珍惜,或人數過多造成互動教學品質變差,最後反而得到反效果。
為了達成目標,首先我們制定一個有審核機制的競爭型申請,而且都是國外審核委員在審,每一個申請案都被三個國外的審核委員看過,還討論了好幾次才決定最後的名額,也可避免在臺灣的委員受到人情壓力的影響。被選上的優秀學員,所有支出基本上都由FISS支付,他們完全不需要付一毛錢,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從頭到尾都要參加。再來,為了讓學生覺得能被選上是一種光榮、值得驕傲的事,我們的網站有每個學員的照片與介紹,希望藉由網頁上每屆被選上的學員照片、背景與專長,讓將來每一屆的學員能形成一種連結、一個小小的社群,互相幫忙、互相合作。
話題八: 籌辦FISS的期待是什麼?
如同之前所說,如果今天只做一屆,那真的就是像煙火,看煙火這樣爆爆爆很爽,但爆完就沒有了。所以我覺得永續經營的問題,是我們最需要去努力的。剛剛提到很多現實面,這都是我們希望克服的。不過也因為辦這樣的活動,我們都學習很多。知道如果真的想要把這件事情辦好,就不可能不食臺灣煙火,完全的理想性,因為那也是痴人說夢,就像正崙講的,你這樣的想法在臺灣永遠做不出事情。所以今天真的要在臺灣做些改變、做些事情、而且下一次希望還能更進步,雖然有些東西該堅持的我們會堅持,不能妥協的也不會妥協,但同時間也必須要學習臺灣是怎麼運作的。
當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一起在做事的時候,其實就是一個很開心的過程。雖然做研究也好,帶學生也好,都是自己想做想拚的,可是同時間自己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又會覺得說,今天我好像可以再多做些什麼更有意義的事情。今天我有現在這樣的位置,是因為我真的比別人聰明嗎?我不覺得。我覺得很多時候一路上真的是遇到了很多貴人,受到了很多幫忙,也有很多時候是我的運氣很好。所以我們大家的想法都是,如果今天可以做件事情幫助其他在臺灣同在一條路上的年輕的學生們的話,這就是我們大家想做的事情⋯⋯【完整訪談版本詳見《科技報導》網站。雖然網站中幾萬字的逐字稿很長,但強烈建議您耐心看完,一同感受臺灣年輕學者為臺灣所熱情付出的心血!】